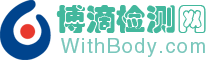近年,合成毒品滥用低龄化趋势明显,亟须禁毒社会组织参与戒毒康复工作。这一过程中,很多禁毒社工加入进来,与毒品“宣战”。
仲文已经5年没有再碰毒品了。因为好奇,15岁的仲文第一次吸食“K粉”;十六七岁流连于“的士高”,频繁“享用”毒品;20岁与警察斗智斗勇,“战场”转至家中;22岁,下决心戒毒。
28岁的香港青年仲文,特意把一件象征着热情和生命的红色运动服穿在身上。他坐在摄影机前,平静地讲述着自己吸毒的“灰色过往”和戒瘾后“无毒的红色青春”。
仲文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给“京港禁毒及外站项目专业社会工作交流研讨会”提供一个“过来人的前车之鉴”,更为了给许多成瘾者克服毒品增添信心。
2014年12月17至19日,研讨会如期举行。
仲文“去毒”
15岁时,仲文碰见姐姐在家里吸食某种“食物”,觉得奇怪,问了句:这是什么?
“K粉!”姐姐这么告诉他。
“K粉”名叫氯胺酮,在各种小手术或诊断操作时使用,可以起到麻醉效应。作为药品,它可以救命,但使用不当,却成了“毒品”。氯氨酮,能够刺激大脑神经中枢,人在吸食一定数量后会产生幻觉,“犹如灵魂出窍一般”。
在姐姐的影响下,仲文第一次“沾上了那个东西”。描述吸食后的感觉,仲文说“头晕,很轻松”。当时,他并不知氯胺酮是毒品,在少年仲文的认识里,只有俗称“白粉”的海洛因才是毒品,“K粉怎么可能是毒品?!”
香港明爱乐协会的禁毒社工李宝康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好奇心是未成年人吸食毒品的主要诱因,而对毒品知识的匮乏让吸食人群‘无知者无畏’。”每当一种新毒品出现之后,吸毒人群又会大幅增加。
李宝康介绍,2013年全港吸毒人数为10069人,21岁以下吸毒人数为1182人。而在1182人中,像仲文一样不到16岁便已经开始吸食毒品的孩子,竟高达619人。“香港吸毒者所吸食的主要毒品便是氯胺酮。”
2003年至2013年的10年间,21岁以下呈报的吸毒人士中,首次在16岁以下吸食毒品的比例在逐年升高,由24%上升至52%。
仲文的尝试随着姐姐搬走而结束。
此后一年,仲文再也没有碰过毒品。然而年轻人的好奇心,驱使他做出了第二次尝试。十六七岁时,朋友带他频繁出入“的士高”,他很快又接触到了毒品。20岁时,他开始外带毒品回家吸食。
这一时期,沉湎于毒品中的仲文有些乐不思蜀。为筹集毒资,亲戚朋友家他没少借钱。然而借来的钱,也不能应付越来越大的花销,他便去银行借款吸毒。债台高筑的仲文,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仲文说:“吸毒引出了法律问题,被警察抓,法律让我戒毒。”
然而,吸毒引发的麻烦还远未结束。几年下来,毒品带给他强烈快感的同时,也让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我发现自己胃痛,小便时也会痛。”
吸毒让仲文承受资金、法律、身体的重重重压,家里人十分担心他,劝他戒毒。
22岁,仲文住进了明爱黄耀南中心,开始戒毒康复。这是一家为青少年戒毒的服务机构。他本打算只住3个月,最后却住了两年半。
“有的人住3个月、6个月就走了,别人走了,我还没走,心情很不好。”仲文坦言,“但是,很多人出去之后,又马上复吸,前功尽弃。”
病友犹如走马灯一样,一拨走了一拨又来。戒毒后又复吸的人,有人因此行凶坐牢,也有人为毒品丢了性命。仲文受到很大刺激,下定决心:一定要戒毒成功。
于是,最初计划的3个月变成了6个月,变成了一年,又变成了两年半。
“过程不容易。”仲文感慨。两年多的时间,让仲文在生理和心理上最终摆脱了毒品。
一线希望成瘾者服务中心的项目总监刘雪莉女士对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介绍,躯体脱毒大概需要10天至30天,而心里康复则需要18个月。她认为,成瘾者戒毒需要两年时间。
仲文用了两年半时间。在这期间,社工不仅帮助他学习与他人沟通的技巧,还教他科学的手段来预防重吸。与此同时,社工把足球引入仲文的生活中,鼓励他培养新的兴趣取代对毒品的关注。2011年,仲文代表香港参加了“无家者世界杯”,取得了很好的名次。
“你愿意改变,便能够改变。”戒毒中心社工这样鼓励仲文。诚如其言,两年多的戒毒努力起到显著的成效,仲文已有5年多的时间没有再接触毒品。
如今,仲文已经完全和毒友断了联系,“现在的朋友都是正面的。”值得一提的是,他正在一家戒毒机构做活动助理,而且还在攻读社工课程,仲文希望将来也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社工。
一线希望
“雪莉,帮帮我……我这里有东西,我非常想用它。”
刘雪莉接到了成瘾者M打来的求助电话。在此之前,M已经脱毒半年。
作为国际戒瘾咨询师和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雪莉帮助过很多成瘾者,并和他们成为朋友。在成瘾者遇到困难,特别是“想复吸”时,很多人会寻求雪莉的帮助,来克服欲望。
从事禁吸戒毒工作近10年,雪莉很明白,几乎每个戒毒者“都会经历想吸的心里挣扎,这是正常的事情”。哪怕是生理已经戒毒,但是心理的坎儿却不能轻易迈过去,总有想吸食的欲望。
这种欲望,会持续半个小时。只要撑过这个时间,吸食的冲动便会降低甚至消失。这个“常识”,雪莉曾告诉每一个她帮助过的成瘾者,“有复吸的冲动很正常,但是能克服。”
不仅是脱毒半年的M,很多已经成功戒毒数年甚至十几年的人,也经常在睡梦中梦见自己复吸。
听到M的求助,得知其正在回家途中,雪莉说:“别着急回家,咱们聊聊吧。”
雪莉所要做的是转移M的注意力,树立脱毒信心,让他度过“半个小时”。通话中,她没提吸与不吸的问题,而只是聊些父母、妻儿的话题,期间也不时说到有些病友去世的消息。
提到成瘾者离世,刘雪莉说:“不要把吸毒者看成怪物,他们是成瘾者,也想寻求改变。但遗憾的是,她身边的人,每年都有一两个人去世,很多人因‘丙肝’离世。”
成瘾者在注射毒品时,很容易感染“丙肝”,一旦病发,器官在很短的时间内会坏死,“人便去了。”每当遇到这种不能改变的故去,雪莉总有种无可奈何的悲伤。
雪莉珍惜每一位寻求改变的成瘾者。在接到病人求助电话时,她会积极为其提供帮助。
通话一个小时,M的情绪终于平复了,最终把毒品倒入马桶,用水冲走了。事后,M对雪莉说:“谢谢你,没有你的帮助,我可能坚持不住。”
这个事情,发生在几年前,但是雪莉一直记忆深刻。“这给我从事戒瘾工作带来很大动力。”目前,她在一线希望成瘾服务中心工作,还经常会给成瘾者讲起M的故事,勉励成瘾者直面问题、克服问题。
35岁的刘雪莉,长发披肩,身材瘦瘦高高,言语中有股平静的亲和力,她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像普通病人一样,成瘾者的治疗也会反复,这是正常现象。当碰到这种情况时,无论是成瘾者,还是他们的家人,很容易心生灰暗和失望。这时,我们社工所起到的作用,就是让他们在失望时看见希望,哪怕是一线希望……”
戒毒康复服务
在过去20年间,香港无国界社工、北京厚德社会工作事务所执行总干事曾开恒见证了国内戒毒康复服务的巨大变化。
“早期被称为‘罪犯’,现在认识到他们是病人。”
对吸毒者认识的不同,产生了两种戒毒方式,早期强制戒毒、劳教戒毒,如今以自愿戒毒、小区戒毒为主,屡戒不成的人才会送去强制隔离戒毒,以后再接受社区康复。
2008年6月,我国实施了《禁毒法》。在该法颁布之前,我国戒毒方式主要由医疗机构负责的自愿戒毒、公安机关负责的强制戒毒、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的劳教戒毒构成。禁毒法将“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结合为强制隔离戒毒,同时给了“社区戒毒”“社区康复”“戒毒药物治疗”一个法律地位。
4年之后的国际禁毒日,温家宝总理签署了第597号国务院令,公布了新修订的《戒毒条例》。此条例下,强调了自愿性的社区戒毒及社区康复。由乡镇政府、街道办和社区戒毒工作小组,依托包括家庭及志愿者在内的社区资源,建立戒毒治疗、康复指导、救助兼备的工作体系。
“这与以往全部由公安管理的强制及劳教戒毒大不相同,这是社会工作人员参与,社区自愿戒毒及康复治疗应该走的路径。”曾开恒评价。
事实上过去10多年,国内多个城市已先后推行了社区戒毒。早在2003年,上海率先推行禁毒社工,协助一些初次吸毒或未犯有严重罪行的吸毒者,还未送其强戒前,在社区里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如今,在深圳市政府戒毒所里,也有了“购买服务”模式,在戒毒所内,社工为戒瘾人员做辅导和关系建立等工作。当戒瘾人员重返社区以后,可以续雇社工,开展社区康复。
我国戒毒康复服务已经有了初步成效,但是面对庞大的吸毒人群,难免有些捉襟见肘。
2014年,我国在册登记的吸毒人员达258万人。“而实际吸毒人员则是这个数据的几倍之巨。”曾开恒介绍,仅就北京而言,近年吸毒人员一直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截至2013年底,北京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达2.5万人,其中35岁以下青少年占74%。合成毒品滥用低龄化趋势明显。他呼吁:亟须禁毒社会组织参与其中。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先后就禁毒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禁毒工作的意见》,从国家战略高度提出“加强禁毒社会组织建设,加快推进禁毒社会化工作进程”的思路。
在这种情况下,由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指导,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北京市禁毒教育基地管理中心、 北京青少年社会工作协会联合主办,北京社区青年汇、北京厚德社会工作事务所承办了首届“京港及外展项目专业社会工作交流研讨会”。
北京厚德社会工作事务所服务主任宋丽娟,期待研讨能够探讨新形势下如何加强禁毒社会组织中社工的发展,提高社工的专业水平,并加快推进禁毒社会化工作进程。
有别于宋丽娟,刘雪莉用更为感性的话语描述了戒瘾工作者的希望,她说:”我需要安宁,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事;需要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事;需要智慧,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而28岁的仲文,正在香港为和自己一样遭受毒品侵害的人们做康复服务,他期待一个“无毒”的青春……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