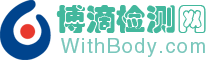张文军,一位与毒品打了21年交道的人。他的身份有很多个,曾经的吸毒者,有6年良好操守的成瘾者,启明星北京成瘾者服务中心的志愿者。
因为吸毒,张文军付出了最惨痛的代价。6年来,他一直尝试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拯救吸毒者,然而事实远比他想象的严峻得多:吸毒年龄越来越小,毒品越来越脏,以贩养吸越来越多……
“北京毒品圈水很深,让我寒透了心。”张文军说。
张文军简介:
张文军,1968年出生。
他是北京第一批“富”起来的吸毒者。1992年,普通工人的月平均工资不过三五百,而24岁的他已经资产百万。那个年代,吸毒是炫富的一种方式。张文军每天吸食海洛因的费用至少是1200元……因为吸毒,生意一落千丈。
2003年,因为吸毒,张文军在女儿出生前10天的时候被劳动教养。
2005年,刚走出看守所不到两个月,张文军再一次因吸毒被抓。这一次,亲手将他送进看守所的是他的亲生父亲。
2006年父亲去世时,兄弟姐妹包括母亲在内没有一个人通知他,他们已经不把他当家里人了。“因为吸毒,气死了父亲!”这是张文军一辈子也洗不掉的罪名。
2007年,张文军开始回头,从一名吸毒者到一名戒毒志愿者。6年来,张文军顺利完成了角色转变,在毒品诱惑面前保持了良好的操守。
但让他深深感到不安和害怕的是:今天的毒品圈子远比20年前更扩大了,充斥着淫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沉迷其中……
“我真的害怕下一代重复我的老路。”张文军无奈中带着绝望。
溜冰 十几岁小孩的致命诱惑
“20多年前,海洛因害了我们那些先富起来的人,我们一度把它当成炫富的资本。而现在,冰毒比海洛因还害人,在一些娱乐场所它成为年轻人追时髦的减压方式。”
——张文军
“我今天又溜了冰……”“走,今晚一起去溜冰……”听到这些话,很多人可能会想到运动的“溜冰”,但当这些话出自吸毒者之口时,可就大不一样了。吸毒者所说的“溜冰”,是指吸食“冰毒”。
“怎么办,我侄子也溜冰了。”一位成瘾者找到张文军,无助和慌张全部写在脸上。成瘾者的侄子叫晓兵,23岁,竟然已有六七年的吸毒史。据证实,晓兵在上中学时,14岁第一次接触了毒品。
“三哥(指张文军),我们溜冰是为了减压。”当眼前几位20多岁的女孩说出吸毒的真正原因,张文军显得有些惊愕。她们都是外人眼中的高级白领,精明能干,光鲜靓丽。为了排解紧张的工作压力,她们每到周末便聚在一起集体“溜冰”。
“三叔,你能找到冰吗?”两个月前,张文军突然接到自己亲侄子的电话。他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五雷轰顶的感觉,脑子瞬间一片空白。“能找到,你来吧。”张文军决定先把侄子骗过来再说。一番追问,确认侄子没有吸毒而是代朋友问问,他才深深舒了一口气。
冰毒的吸食者以年轻人为主,涵盖各个阶层,有在读学生、公司白领、企业老总,也有家境阔绰的青年男女。朋友拉朋友,源源不断地加入到“溜冰”行列,形成了一个个圈子,彼此间互称“冰友”。
“冰毒最吸引年轻人的就是它能让人极度兴奋,而且适合群体吸食,很多年轻人把它当成娱乐。”张文军感叹,在一些娱乐场所,想找到“冰”并不难。生意场中流行的一种应酬就是请人吸冰毒,有些十六七岁的年轻孩子过生日,互相送的礼,有时就送一袋“冰”。
“很多人并不清楚冰毒的危害,认为新型毒品不会成瘾。”张文军很担心自己20年前的悲剧重演。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是,吸食海洛因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于是毒品在很多有钱人中间流行,当时他们并不知道海洛因的危害有多大,结果毁了自己的一生。
“如果有机会,你愿意尝试一下吸毒吗?” 有机构曾做过一次调查,面对这个问题,7%的学生竟回答愿意,理由是:“听说一两次上不了瘾,可以试试。”这样的结果让张文军感到害怕。
据警方统计,青少年吸毒的成因,38%是好奇,12%是受亲友影响,26%是精神空虚,24%是被引诱上钩。可见,很多“冰友”是在“免费尝试”“不上瘾”“能减肥”等错误的认识蒙蔽下涉足毒品的。
“据我所知,在一些娱乐场所,经常有人免费提供一些摇头丸给寻求刺激的客人,尤其是十几岁的孩子。这其实是一个跳板,一个引子,等你上瘾了或主动寻找更刺激的方式时,就玩大了。”
“我吸过毒,深受毒品之害,吸毒的年轻化趋势让我感到恐慌。”张文军说。
催情 幻觉击垮做人底线
“与海洛因相比,冰毒是一种更可怕的毒品。海洛因是镇静剂,可以一个人静静地吸;而冰毒是致幻剂,常常是一个群体共同吸,冰毒会让人产生精神幻觉,在幻觉的作用下可能会出现各种暴力行为,甚至发生集体性行为。”
——张文军
“快救救我的孩子吧,他可怎么办啊!吸毒回家他就像个疯子一样,完全没有了人性,对我都敢动手动脚的……”当张文军接到一位吸毒者母亲打来的电话求助时,作为成瘾者,他自己都觉得有些无地自容。
“我知道,您儿子肯定是吸食冰毒产生了幻觉。他有可能跟‘冰妹’一起吸的,现在还在幻觉当中。两三天后,毒品效力过去了,人自然就正常了……”张文军尽可能平和地向这位母亲解释。但内心他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是自己过去吸食海洛因时所没有的,“冰毒到底有多可怕,怎么能让一个人完全没有了做人的底线!”
虽然自己没有吸食过冰毒,但张文军近几年整天跟吸毒者打交道,对新型毒品了解了很多。他知道,吸食冰毒后,人会极度亢奋,两三天精力旺盛,不睡觉。同时,吸食者的大脑还会出现一种精神幻觉,在这种精神幻觉的支配下会出现各种暴力行为,比如认为别人在背后说他坏话,甚至会看到被人追杀等。在这种幻觉支配下,会出现杀人、自杀、放火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据我所知,很多人喜欢冰毒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助性’。说白了,冰毒是最好的催情剂。”张文军坦言,吸食冰毒会诱发人的性欲亢奋,而且对性伴侣不加选择,犹如潘多拉的盒子一打开,万劫不复,“冰毒和性欲、淫乱往往是连在一起的”。
冰毒与海洛因不同,吸食海洛因不需要女人,几个男人在一起也可以吸食,但是吸冰毒必须要有女人。有人曾统计过,吸食传统毒品的男女比例一般是8∶2,但吸食冰毒等新型毒品的男女比例则变成了5∶5。
这几年,随着冰毒的泛滥,在娱乐场所专有一类人叫“冰妹”。这些“冰妹”先跟客人一起“溜冰”,然后再进行色情服务。不得不承认,这是冰毒等新型毒品带来的一种新兴“职业”。“怎么说呢,溜过冰的小姐与没溜过冰的小姐是绝对不一样的,正常情况下,虽然是做小姐的,但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羞耻感,即使是向客人提供性服务,也会相对注意隐私性,但是溜过冰的小姐正常的思维会被毒品破坏掉,会在没有正常知觉的情况下,完全沦为供客人取乐的性工具。” 当然,这种行为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各种性病、艾滋病直线上升。
加了老鼠药的毒品 你吸吗
“如果告诉你,你花高价买来的海洛因里加进了老鼠药,你还会吸吗?那么我告诉你,不仅加老鼠药是真的,还可能加进了石灰、墙皮等一切可能的东西……”
——张文军
“现在的毒品没法吸,里面简直太脏了,哪还是毒品,简直是毒药。”张文军在规劝成瘾者时,经常这样说。
作为与毒品打了20多年交道的圈子里的老人,张文军知晓毒品圈子存在的很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现在黑市上卖的毒品都不纯,几百块钱买来的一克海洛因,里面被掺杂了各种杂质。最早时候,海洛因贩卖者还是有一些良知的,一克海洛因,加两倍底粉。所谓底粉,是一些制药厂家用来做药片用的。这样的毒品,虽然不纯,但至少无毒。”
“但后来,药片不用了,因为成本高。一些贩卖者为了节约成本,想尽了各种丧尽天良的方法,各种东西都可以做底粉,什么石灰啊、墙皮啊、淀粉啊、白面啊等等,势必这会影响吸毒的效果。对很多人来说,吸毒不就是为了追求一霎那飘的感觉吗?于是,贩毒者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在海洛因里加入老鼠药。吸入后,重新又有了飘的感觉。其实,人都快毒死了,能不飘吗?”张文军因为经历过,所以对此更为痛恨。
“不瞒你们,你看我这胳膊,就是当初注射不安全的海洛因留下的疤。”右侧胳膊小臂处,大大的伤疤很是明显,而且已经形成硬疙瘩。张文军回忆,自己从1992年开始吸毒,到1998年身体经常注射毒品的地方开始出现严重溃烂。“那时很多吸毒者都出现了同样情况,因为毒品纯度不好,打到哪里,哪里就会溃烂。肩膀、屁股、大腿……有的甚至被截肢”。更为严重的是,张文军经常听到某某成瘾者死在厕所里、死在家里的消息,死亡原因一般有两种,一是一次性注射毒品过量死亡,另一个则是毒品中含有毒鼠强等剧毒中毒身亡。
其实,对于很多吸毒者而言,毒瘾上来,自己也在作贱自己。张文军从小就有晕针的毛病,但唯独吸毒那段时间,毒瘾一旦上来,全身都被毒瘾控制了,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晕针,拿着注射器就往自己身体里扎,满脑子全是渴望。“说出来你们可能不相信,很多毒友在外面条件不具备时,本该用注射液溶解海洛因,可以换成矿泉水、自来水,甚至连地沟水、河里的水都敢用,那一刻,身体溃不溃烂、中不中毒、丧不丧命都不管,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先注射上毒品再说。”
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追捧的冰毒等新型毒品,张文军坦言“质量同样不保证”。
“冰毒”即甲基苯丙胺,又名甲基安非他明、去氧麻黄碱,是一种无味或微有苦味的透明结晶体,形似冰,故俗称“冰毒”。“冰是化学合成毒品,其主要原理就是运用化学元素控制神经中枢。冰毒的制造工艺很简单,自己也可以生产,但兑入的化学元素越多,伤害越大。”
“因为纯度不好,在国内至今还没有可注射的冰毒,都是用冰壶烫吸。”张文军透露了这样一种说法。
以贩养吸 踏入另一条死亡通道
“一个毫无经济收入的年轻人,染上毒品后,一个月2-3万块的毒资无疑是最大的经济负担。毒资从哪里来?除了偷、抢、要外,以贩养吸是最后的下场。当然,这也等于踏入了一条死亡通道。”
——张文军
在北京与经济学家探讨毒品经济时,有一组数据他们多次提到:2004年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已超过2亿,全球毒品每年销售总额大约为8000亿至1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0%,这一数字高于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收入。这一组数,在经常要穿着防弹衣的缉毒专家眼里,是毒品经济中另外一个重要环节,那就是险象环生的毒品贩运。
“在毒品贩运中,很多都是吸毒者在以贩养吸。”张文军说。
各地的情况表明,绝大多数青少年吸毒者最后变为了贩毒者,滑入了毒品犯罪的深渊。这些青少年一般是从吸毒开始的,当毒瘾不大,工资收入和储蓄尚能维持时,他们是单纯的吸毒者。随着毒瘾增大,所需资金的增多,原有的财力难以支撑吸毒所需时,便以贩毒养吸,由毒品的被害者变为害人者,发动更多的新人加入吸毒行列。吸毒和贩毒这对联体怪胎相互依存,推波助澜,形成恶性循环。
据某地一项调查表明,在毒品犯罪人员中,有90%以上是贩毒兼吸毒,纯粹的制造毒品者、运输毒品者、贩卖毒品者和持有毒品者不足10%。
以贩养吸的利益空间是巨大的。以冰毒为例,从加工厂生产出来的冰毒,以每克170元至200元的价格卖给第一道贩子,随后每倒一手,贩子便会加价。进入北京黑市后,每克会被卖到600元左右。但这仅仅是贩卖链的开始。
从生产地来源的冰毒纯度很高,进入黑市后,有贩子会分装成小包,掺入面粉、墙灰等,再以每包800元不等的价格卖出。因为纯度大大缩水,以贩养吸者每卖两克,从中便可获利近千元,同时也解决了自己的吸食来源问题。
有钱吸毒没钱吃饭,这是很多人鄙夷吸毒者时最常用的一句讽刺的言语。但对吸毒者而言,这并非讽刺,而是连他们自己都摆脱不了的事实。毒品是控制中枢神经的,它可以让吸毒者忘记吃饭,但不能忘记毒瘾。毒魔来时,命都是次要的,何况是犯罪。
隐藏 成最后的生存之道
“自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对吸毒人员申请驾驶证采取了‘零容忍’态度:3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这一政策,可能会让更多的吸毒者走入隐藏状态。”
——张文军
“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批最先富起来的吸毒者基本家财散尽,如今四五十岁的他们有的正从事出租驾驶性工作,驾照是唯一的执业技能。吸毒禁驾政策施行的直接后果便是,驾照注销意味着他们的生活来源也掐断了。”张文军说。
“不仅如此,很多仍在服用美沙酮替代治疗的成瘾者,如今也不敢再去治疗了。因为对他们而言,进行美沙酮替代治疗,会100%注销驾照;如果不去,50%会注销,另外50%的机会是保留,至少多一倍的希望。”张文军无奈地说,“谁敢保证隐藏状态的他们不复吸呢?”
97%的戒毒人员都会复吸,这是“启明星”统计出来的令人震惊的数字。6年来,张文军在保持良好操守并拯救更多吸毒者的同时,越发深刻地意识到,“无聊无事无工作、受歧视、毒友引诱是引起复吸的最主要原因。”
据调查,中国60%的吸毒人员是无业青年;有工作的人吸上毒后,70%以上失去工作。而来自“启明星”北京成瘾者服务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戒毒后95%以上的成瘾者都处于无业状态。“启明星”曾开展过一个项目,试图将成瘾者推荐给用人单位,工资单位只负责一半,另一半由启明星项目负担。即使这样,项目仍然没有进展下去,找了100多家用人单位,都无果。
“每一位成瘾者都渴望回归正常人的生活,但回归之路布满了荆棘。解决戒毒者的再就业问题是一项系统的工程,不能靠公安、社区单打独斗,要社会保障部门完善社保,卫生部门提供卫生服务,工商税务部门提供就业岗位,政府出台创业优惠政策,街道办事处加强跟踪管控等等,形成戒毒康复者社会接纳体系,多管齐下,才能解决。”张文军说。
“做这个群体的帮扶救助太难了,大环境改变不了,就存在复吸的危险……”6年来,张文军头一次萌生了退意。
新闻观察
特邀专家 刘志民
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研究所副所长,药物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主任。
新型毒品不上瘾纯属谣传
目前,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总数在150万左右,其中新型毒品吸食者占到了30%。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新型毒品是一种时尚和潮流,并不会上瘾。真是如此吗?
刘教授告诉记者,苯丙胺类毒品(以冰毒、摇头丸为代表)对人体身心的危害突出地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滥用时出现精神兴奋、行为亢奋等中毒反应,许多人在一些娱乐场所滥用后剧烈活动出现生理透支,而停用后又出现嗜睡、精神萎靡等中枢抑制症状。第二,滥用可导致不同程度和类型的精神病性症状或苯丙胺中毒精神病,可出现幻觉、精神错乱、躁狂,一部分人还可发生精神分裂样症状。第三,在用药后急性中毒情况下导致的行为失控,一是不可控制的易激惹、伤人、自伤甚至暴力行为,二是在毒品的作用下产生性冲动、滥用者群体性性乱行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性病、肝炎、艾滋病的感染传播。
关于对冰毒、摇头丸等苯丙胺类兴奋剂是否具有成瘾性的问题,刘教授给出了明确的回答:苯丙胺类毒品具有强烈的成瘾性。药物依赖分为身体依赖性和精神依赖性,与传统毒品相比,新型毒品的精神依赖性更为严重。精神依赖性是指毒品对大脑“奖赏”系统刺激后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精神效应,用药者为追求这种特殊精神效应而反复使用药物的强烈心理渴求,以及在这种心理渴求驱使下强迫、周期用药的行为,精神依赖性实质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成瘾”。同身体依赖性不同,精神依赖一旦产生就很难彻底清除。俗话说,一朝吸毒,十年戒毒,终生想毒。
记者手记
不该是一场孤独的战斗
“我真的寒心了,做完这一年我不想做了。”采访前和采访后,张文军反复强调着这样一句话。我相信,他不是随随便便说出的这样一句话。
这压力来自方方面面,有吸毒者的,有家庭的,有社会的,也有政府的。现在的张文军有种“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的感觉,之前他以为,海洛因等传统毒品贻害了很多人,于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帮扶成瘾者回归社会上。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回归之路没有起色,而仅仅几年的工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又陷入了新型毒品的漩涡中。“我真的很害怕,害怕我们那一代的悲剧重演。”
采访中,刘志民教授严肃地告诉记者,目前新型毒品滥用成瘾的治疗及预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是禁毒工作面临的一个新的严峻挑战。从我国来看,许多“新型毒品”滥用者已发展成习惯和强迫性使用,越来越多的滥用者出现苯甲胺中毒精神病,许多人就医的主要原因是治疗解决因吸毒造成的精神病性症状。此外,由滥用毒品引发的性冲动、群体性性乱行为所造成的公共卫生和社会危害是不能低估的。
让青少年认识到新型毒品的危害并自觉远离并非一日之功,也非某个政府部门的独自责任。青少年成为吸食新型毒品人群的主体,值得我们执法者和每一个社会公民反思。毕竟,新型毒品腐蚀的不只是青少年的身体,更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环境。